小镇阿姨们想象着法国织的毛线比基尼,真的到了法国
八年以来,阿姨们依然不知道这个“法国公司”的来源。毛线串起一个西南乡镇的想象世界,而搭建这个世界的胡尹萍,也尝试在其中还原她儿时在小镇感受到的国营工厂氛围,尽管这样的创作方式在功利社会、内卷世界里显得如此乌托邦。
“那个盆地里有一群阿姨一天到晚都是在胡思乱想,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去做她们胡思乱想的工作。”
2023年秋,胡尹萍到了巴黎,参加Paris Internationale 艺博会(国际巴黎艺术博览会),这是她第三次为小芳艺术项目到法国布展。这次带的作品是毛线织的比基尼,来自她长大的四川小镇的阿姨们。2015年以来,胡尹萍以虚构的法国公司代理人“小芳”的名义,向她的母亲和家乡阿姨们定制毛线织物产品。如今,阿姨们想象着法国的一片海洋织出来的毛线比基尼,终于到了巴黎。
这座四川小镇上,“法国公司”是阿姨们的想象源头。她们在小芳基地自选毛线,以绿色居多,一开始织的是形态各异的帽子,它们出现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展厅、美国反特朗普大游行的现场、爱尔兰“绿帽子节”……后来织品形态越来越丰富:“脏话冲击波”(把想骂坏人的脏话织出来),猪肉铺阿姨织的“猪大肠”,每家每户织的各自家庭的旗帜,还有面对危险时保护家人的毛织“香蕉皮”、“狗”、“仙人掌”…… 在农忙和带孩子的间隙,这些阿姨用毛线织着她们对生活的理解。
“见好就收。”2016年,胡尹萍在北京箭厂空间完成小芳艺术项目的首次帽子展览后,有朋友担心项目太赔钱,这样劝她。胡尹萍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,用“乔小幻”这个商业雕塑艺术家身份卖出的雕塑收入,来补贴小芳的制作。而这一切的最初原因是她想收藏母亲的时间。
2015年,胡尹萍回四川老家,看到母亲一年的时间被两大包帽子打包,被低廉的价格收购。她想购买母亲的帽子,被母亲拒绝。回北京后,她找了一位朋友扮演“小芳”,并为“小芳”编造出“某法国公司中国CEO”的身份,由“小芳”出面以较高价格收购母亲的帽子,请她随心所欲地织帽子。
然而小镇没有秘密,镇上的阿姨们找到胡尹萍的母亲,也想加入小芳项目的制作。在1990年代,剿丝一度是镇上阿姨赚钱养家的渠道,在经历国营剿丝厂的集体下岗后,这些阿姨大多成了被淘汰的城市剩余劳动力,如今织毛线是她们打发时间和赚零花钱的方式。
▲胡尹萍
现在小芳项目扩展到五十多位织毛线的阿姨,有《小芳》《雪白的鸽子》《安全感》《联合国》《标准配置》等五个阶段不同年份的命题创作。创作的背后是艺术家的复杂工作。而与胡尹萍创造的工作乌托邦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艺术家所面对的残酷的、明码标价的艺术市场。直到现在,阿姨们依然不知道这个“法国公司”的来源。
以下是胡尹萍的讲述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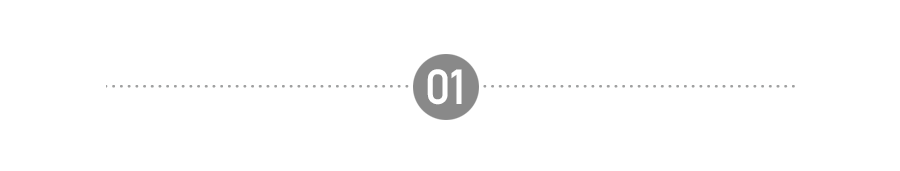
阿姨很开心,艺术家很累
每次到巴黎布展我都会比较开心,因为小芳这个项目本身跟法国比较有渊源。每次有项目,我们跟阿姨说的都是法国公司需要订单,邀请阿姨们制作,再支付相应的费用,这个法国公司一直存在于阿姨们的心里。一开始在制作时,我们对阿姨说法国有一个沙滩,我们要在海滩上做毛线比基尼秀,她们就想象一片海滩,为自己和家人做一套毛线比基尼。
小芳在国际上有挺多这样的交流和工作,这次法国的展览面向的是更专业的艺术人士,对应着大量的策展人和美术馆负责人。我也希望小芳进入一个更深入、更国际的交流和对话。对大众来说,小芳可能是一个相对温暖的故事,但对我来说它是很具体的工作。在阿姨背后,是我们整个团队非常严谨和专业的工作。大家可以用自己的任何方式进入和认识这件作品,但它本身是当代艺术作品的底色。
阿姨们的针织作品都放在我的仓库,在北京周边一个村子里。阿姨们都是很开心的,但是艺术家比较辛苦。小芳团队六个人需要处理大量具体而琐碎的工作。阿姨们不管的,她们织的时间是不固定的,线是自己选好领回家做、从中获得一些费用,不管是挣钱也好,打发时间也罢,或者是所谓“思考”也行。
刚才给你打电话前,我在跟美术馆对接这次展览的运输和货单,要整合阿姨的所有工作,需要做一些非常具体和严肃的工作,实际上工作量蛮大的。
对于小芳的项目,经济撑不下去的时候太多了,养小芳每年要花挺多钱的,会靠卖“乔小幻”的雕塑来养活小芳,但去年开始有点持平的意思了。去年小芳在上海做完展览,可能很多人对小芳认识也多了一点,去年居然盈利了800块,如果能自循环就不用再去养它了。
现在小芳做新的项目是在南京万象天地开小芳银行。小芳的作品本身具有极强的公众性,除了在美术馆和画廊的展览对话,它在面对真正的大众时有什么反馈和可能性,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。因为美术馆和画廊面对的人群实际上是经过筛选的,但在商场里面对的是真正的大众和现实,没有保温箱的保护。这家银行的概念是,我希望未来的银行是毛线做的,我希望未来的货币也是毛线做的,我希望未来的武器也是毛线做的。
上世纪90年代前,整个社会物质匮乏,毛线作为阿姨们的手艺,可以让家人吃饱穿暖,而现在毛线的价值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织毛线?去年在上海办展时,一些人对我说,他们在疫情期间会做大量针织。小小的织物实际上能带给你很多惊喜和回馈,因为手工本身就是带有治愈属性的,你用时间交换的是一个物,这是一个最原始的劳动力的交换。
在小芳的展览中,我碰到一个女孩,她在怀孕时想象着肚子里的孩子,为孩子织鞋子和衣服。我遇到一位驻华外交官,她在新冠疫情期间做一些毛线织物。她认为自己做了一个丑丑的老鼠、做了一个丑丑的小蛇,这位满头银发的女士说起自己的织物时,腼腆得像一个小姑娘,我太喜欢她做的这些东西了,也能感受到她内心的那种温暖和治愈。
小芳的帽子是终身保修的,我不希望帽子买回去以后,破了一个洞,你就把它扔了,这样对手工劳动是很可惜的。小芳之后不管是做什么项目,永远包含着“补洞”的功能,我们也会向周围社区免费开放补洞,希望能形成这种社区性。不是一个东西坏了一点,我们就扔掉了。我觉得遗弃这个事情大家都干得太多了。
城市的剩余劳动力,镇上的剩余时间
为了保护视力,我给我母亲的毛线大部分都是绿色的。因为绿帽子在中国的语境里寓意并不好,阿姨们拿绿毛线织各种帽子时,还是有些质疑。后来VICE(美国的一家新媒体)要给小芳艺术项目做采访,帮忙找了买绿帽子地方——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节,这个节日的的传统颜色就是绿色,给我们订了好多绿帽子。
在爱尔兰,这些人戴着帽子参加节日集会,阿姨们看到那些现场照片也很高兴。同一个东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意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,我也希望让阿姨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很丰富的。但她们能开心地去做自由的选择,我觉得是更重要的。
2015年我回老家,近乡情怯。因为回家次数很少,我想知道母亲平时在做什么呢?当她把两大包手织帽子摆在我面前的时候,我才知道,噢,她原来这一年织了这两大包东西,被别人廉价收购走。而且原材料太伤手,线非常硬,又极度粗糙。做针织的愉悦感和幸福感她是没有的,她只是打发时间,仅剩这一个理由。
我觉得还不如我自己来收呢,但我母亲不让,我就请朋友帮我扮演法国公司“小芳”,约她做帽子,随她怎么做。2015年微信还没这么普及,我母亲在老家也用不上微信,但因为要和“小芳”对接工作,微信成了她必须要掌握的工作技能。因为工作,她学会了上网、寄快递,以前快递上都是写我父亲的名字,因为“小芳”,后来寄快递时她在快递上都是写自己的名字。
其实我们对参与小芳项目的阿姨做过调研,她们几乎都是被淘汰的城市剩余劳动力,进城务工的女性55岁之后很容易被淘汰。在城里当送货员、保洁,到一定年龄,哪怕你是有多年经验的保姆,恐怕55岁以后也极难在大城市找到工作,这就是城市化进程中这群阿姨面临的问题。阿姨们差不多五十多岁就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返乡,为自己的孩子带孩子,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开小卖部,空闲时间就拿毛线织东西、赚零用,在镇上是很常见的。
自从“小芳”出现后,阿姨们就不给别的地方织东西了。其实阿姨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情,有些阿姨在农忙时肯定顾不上做我们的东西了,一年就几次插秧、收割,中间有很长的闲置时间,有些阿姨在家带孩子,孩子上学后就是闲置时间。还有些阿姨有自己的小店,没生意时她就可以做小芳的事。小芳实际上是填充着阿姨们的剩余时间。
在小芳的第三个阶段《安全感》,猪肉铺的阿姨一开始想象不到要织什么。我们会一点一点引导她,在她最忙的时候,小芳给她打电话,“如果此时此刻有人要把你的猪肉铺给抢了,你会用什么样的武器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?”她手里正拿一坨大肠,说如要抢我的话,我拿大肠扔死他。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。到她不忙的时候,我们会把她自己说的话重复给她,鼓励她织这个。
关于小芳,大家都在讨论阿姨的想象力,实际上是艺术家的想象力在支撑着她们的工作。阿姨们是没有想象力的群体,但她们可以被引导,她们要做的就是面对真实的自己和自己的生活。每次其实我都知道她们在做什么,但看到做出来的东西时仍然很惊喜。
最开始,小芳在周末给我送来我母亲做的那些帽子包裹,每次打开包裹我都特别多惊喜,这种惊喜还不重复,我在和我母亲无比熟悉的情况下,突然发现她有个我不知道的技能,我知道她永远在做帽子,但不知道她花里胡哨乱七八糟做了那么多好玩东西。
阿姨们依然不知道小芳背后的事情,实际上她们知不知道也不是那么重要,因为她们也没那么在乎这个事情,只是我不想让我母亲知道。前段时间我母亲到北京待了将近两个月,我们就把整个工作室的织物全部清空,没留一根毛线。我母亲玩一个星期就待不住了,于是我又请“小芳”出面到工作室给她一点活做。
其实我母亲这边,我一直没有给她太多的主题,我收藏的不是具象的织物,或者要求她动什么脑筋,不需要她这样。我希望收藏我母亲生命的一段时间。我希望她更自由一点,不想把她女儿的事变成她的事,那样她太累了。为她自己活挺好的,已经这个年龄了,赶紧为自己活吧。
凝固的时间,波动的海浪
1990年代,我母亲和镇上阿姨们是在镇上的剿丝厂上班。但中国的纺织业进行大洗牌也是在1990年代,那时候形成了大量的下岗,我母亲和阿姨们也在其中。剿丝就是蚕茧用高温机器蒸煮以后,一根一根地理出蚕丝,八根丝缠成一根线,做好的蚕丝最后运往外地。
工厂的机器永远是匀速地转着,人在更替,我母亲就在这个流水线上工作。我的童年就是坐在那个工厂的大机器上面,阿姨们换岗工作,这个吃饭时给我喂一口,那个来吃饭给我喂一口。我的整个童年到小学,都是在那个氛围里度过的。
那种人和人的熟悉感非常好,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记忆,后来小芳有这么多阿姨参与,我感受到的都是当时那种很熟悉的亲切感。在我小时候,我妈的单位会发各种福利,发个保温杯、发点洗衣粉呐,我觉得这个特别好,会让家庭成员对她的工作有认同感,我们在小芳里就保留了这个。这几年,我们能发给阿姨的东西已经发得差不多了,从杯子到水果、洗衣粉,从锅碗瓢盆到一切小家电我们都发了个遍,最近因为冬天快来了,我们又买了好多被子给阿姨,现在已经不知道该发什么了。
第一次在箭厂空间办小芳的展时,朋友劝我“见好就收”,这个建议是很真诚的,作为朋友劝我及时止损。可是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作品,小芳对我来说是我跟母亲的一个很真实的生活现场,所以它不是一个见好就收的事情,尽管我知道它赔钱。
我们一开始全是她们随便织,我玩命收。后来发现这样不对呀,租多大的仓库都不够这几十个阿姨织的,人家做了,你就得付钱,付了钱就要帮她们做织物的销售,销售是需要才华的,我没这个才华,几个美术馆又能卖多少帽子呢?这事太残酷了。我们主要是在工作室里工作,其实很少去了解这个世界经济的运营规则。在小芳的过程中,我们非常真实地参与这种工作也是有意思的一点。
小芳这个作品,它仍然是植入到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因为其实对一个艺术家来说,十年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作品。但是我跟小芳是一个共同成长的关系,小芳一边植入到阿姨的生活,一边植入到我母亲的生活和我的生活。我也算过一笔账,比如说我去做别的东西,也会把这些钱付给工厂和制作单位,但当我付给阿姨,实际上没形成一个艺术系统的内部循环。把这一部分费用投入到阿姨的身上,我觉得就是投入在自己人的身上,让我比较愉快。
下个月我们要去墨西哥布展。小芳做到现在,观众的反应实在是太多了,大家有喜欢的,也有不喜欢的。我把那个比喻从一开始用到了现在,我是一根牙签,同时也是一个观察者。阿姨们就是水母,我用牙签戳一下水母,水母就在大海里姿态各异地晃动。批评也好,赞誉也好,或者是采访、展览也好,其实都是在大海里蝴蝶效应的一个环节。我的工作就是扎完那一下以后,去观看这些反应和她们的姿态,不管水母的姿态,还是大海里产生的波动、浪花,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极其美好的事情,因为它发生了反应,而不是固有的、保守的东西。
未来,我希望有很多人像那位驻华外交官一样给我看她的作品。我希望大家不要羞涩,勇敢面对自己,手工东西真的不存在丑陋,都是极度有质感的存在。我想重新定义毛线,我想重新定义小芳的文化属性。我现在主要在做这样的工作,也在持续推进。其实艺术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台下很安静地工作,至于被看到或是不被看到,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和讨论,都是很外在的事情。
四川是个盆地,我们镇上那边有一条河,它跟中国所有的小镇一样,非常凝固的人群,非常凝固的时间。小镇上就是那么点人,但阿姨们想象着一个法国公司,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挺酷的,那个盆地里有一群阿姨一天到晚都在胡思乱想,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去做她们胡思乱想的工作。
本文转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